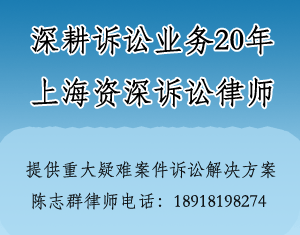【案情】
原告周某和被告龚某于2019年4月成立被告鼎岚公司并开业经营。其中周某持股80%,任公司执行董事,龚某持股20%,任公司监事。公司章程规定,执行董事、监事任期三年,执行董事是公司法定代表人。2020年3月,周某和龚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龚某以50万元购买周某所持全部股权,公司债权债务均由龚某承担,但未约定变更公司股东、执行董事或法定代表人登记。协议签订后,周某未再参与公司经营,公司登记事项亦未变更。2020年4月,鼎岚公司由于未通过营业前消防监督检查被责令停业至纠纷成讼。同年8月,由于在支付装修款、职工工资引发的纠纷中未履行法院判决,鼎岚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周某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同年12月,周某起诉请求判令变更鼎岚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登记。
【分歧】
本案关于判决变更鼎岚公司股东登记并无争议。但是否判决变更鼎岚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尚有分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的前提是公司有此意思表示。法定代表人的更换属公司内部治理事项,法院应对此力行谦抑,即在不能证明公司已做出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决议或相关安排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应直接判令公司办理变更登记。且原告在有能力使公司变更登记时未做出安排,系怠于维护自身权益,后果应自行承担。
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法定代表人是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理应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告徒有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名,不持公司股权,不再参与公司经营,也无法通过公司自治途径推动公司就变更法定代表人作出决议。若不支持其诉请,则与法定代表人制度的立法目的不符,且原告因此承受的法律风险持续存在,形成僵局。故在当事人拒绝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又已不是公司股东的情况下,应当支持原告全部诉请。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平衡处理公司自治和人格保护间的关系。由与公司没有任何基础法律关系的人担任法定代表人,既不符合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宗旨,也有损个人名誉、影响个人生活,司法权应予以干预。但在公司没有作出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意思表示时这一干预应当十分慎重,需实质地探究法定代表人与公司间的关系,区分不同情形审慎处理,防范公司经营异常时法定代表人借此规避责任,依法保护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起诉公司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的,应当区分情形予以处理:
首先,应审查公司有无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意思表示。公司已经作出决议更换法定代表人但未变更登记的,应依据公司法第十三条判令公司变更登记。即使没有决议,但存在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亦然。存在由特定股东指派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等特殊安排的,当该特定股东撤销对相关人员的委托或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时,该指派行为即告终止,公司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未变更的,应判令其限期变更。
其次,公司没有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意思表示的,应当考量法定代表人和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和法定代表人的自力救济情况。在能够确认法定代表人自担任职务始不持有公司股权、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且不持有公司证照、印鉴的情况下,可以认为该法定代表人从未代表公司从事过民事活动,亦缺乏督促公司免除自身职务的能力。此时若公司无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意愿,应当判令公司限期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他人。
最后,公司无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意思表示,而法定代表人曾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现在主张其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请求判令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的,此类公司大多已经处于经营异常状态,法院审理时应当优先考虑保护公司债权人权益,着重审查法定代表人参与公司经营与公司主要负债之间的关系,同时考察法定代表人诉前自力救济的情况,并通过证明责任的分担来合理分配责任。一般地,应由法定代表人就其参与公司经营的情况、公司债务产生的时间、公司债务的内部安排以及曾要求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公司或其他股东可举证证明法定代表人仍实际控制公司或者仍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除非确能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已不参与公司经营,不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且曾要求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未果之外,一般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应秉持意思自治和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准则审慎处理此类纠纷,维护法定代表人制度良性运转。本案中,鼎岚公司没有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意思。周某和龚某在股权转让之时及之后也未曾对公司变更登记进行约定,亦无证据证明周某在被采取限高措施前曾与龚某协商变更登记事宜。龚某实际控制公司后经营时间短,鼎岚公司相关纠纷与公司成立初周某控制时的活动关联密切。在公司对外纠纷未处理完毕情况下,不应由法院直接判决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应当驳回周某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的诉讼请求。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