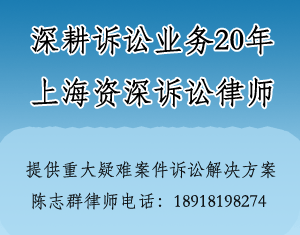——加拿大最高法院“Peoples Department Stores Inc. (Trustee of ) v. Wise”案述评
「摘要」在本案中,初审法院法官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认为公司董事在公司濒临破产时,对公司债权人负有信义义务。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认为公司董事仅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本案被告董事并未违反任何义务。最终,终审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澄清了业界所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义务。不论是与加拿大以前的法律相比,还是与国外其他国家的法律相比,该判决都赋予了公司债权人更加广泛的潜在权利。最为重要的是,该判决未将公司债权人的此等权利与“公司濒临破产”这一要件事实联结在一起。此外,该判决还明确了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总是负有注意义务这一重要公司法规则。
「关键词」债权人,信义义务,注意义务
2004年10月29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发布了Peoples Department Stores Inc. ( Trustee of ) v. Wise一案的判决,这一判决广受期待与关注。本案判决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根据《加拿大商业公司法》(Canada Business Corporations Act,以下简称为CBCA)第122条(1) ( a)之规定,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是否负有信义义务;二是根据CBCA第122条( 1) ( b)之规定,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是否负有注意义务;三是根据《加拿大破产法》第100条之规定,疑问交易的对价是否明显低于公平的市场价。
该案的诉讼进程可谓一波三折,判决的结果也历经反复。1998 年加拿大魁北克高等法院法官Greenberg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主张,认为公司董事在公司濒临破产时,对公司债权人负有信义义务。2003年2月,魁北克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认为公司董事仅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本案被告董事并未违反任何义务。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本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上诉,维持了魁北克上诉法院的判决。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澄清了业界所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义务。不论是与加拿大以前的法律相比,还是与国外其他国家的法律相比,该判决都赋予了公司债权人更加广泛的潜在权利。最为重要的是,该判决未将公司债权人的此等权利与“公司濒临破产”这一要件事实联结在一起。此外,该判决还明确了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总是负有注意义务这一重要公司法规则。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该案的背景事实,然后结合一审、二审及终审判决,就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信义义务与注意义务问题做一阐述。
一本案背景事实概要
本案被告Wise三兄弟是Wise Stores Inc. (以下简称为Wise公司)最主要的三个大股东。Wise公司在加拿大经营商品零售业,并于1992年并购取得了另一家同样经营商品零售业的加拿大公司 People Department Stores Inc. (以下简称为People公司)的全部股份。但由于外国同行竞业者的进入,使得本来就竞争异常激烈的加拿大东部地区的零售业更是雪上加霜。面对如此残酷的竞争环境,Wise公司与People公司同时陷入了财政危机。Wise兄弟意识到,公司的存货采购环节效率特别低下,于是为加强公司的理性化运作和降低成本,Wise兄弟指示两家公司启动“联合存货采购计划”。根据该计划, Peo2p les公司承担了绝大多数Wise公司的存货采购和支付业务,即先由People公司根据Wise公司的需求采购商品,然后卖给Wise公司,再由 Wise公司偿付People公司所支出的货款。实施该计划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 People公司开始持续地扩大对Wise公司的营业债权。截止到1994年6月,财务报表显示,Wise公司已经欠下People公司1800万美元的货款债务。
尽管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促进措施,但Wise兄弟仍然不能挽救Wise公司与People公司直线下滑的财政命运。1994年9月,公司债权人启动了针对Wise公司与People公司的破产程序。1995年1月,两家公司被正式宣告破产。经清算后,许多债权人,特别是People公司的许多债权人的债权不能获得清偿。基于此种情况, People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代表所有未获清偿债权的债权人利益,起诉Wise兄弟,声称Wise兄弟作为People公司的唯一董事,在“联合存货采购计划”的实施中未尽到董事的应有职责。易言之, People公司的债权人认为,Wise兄弟经由以牺牲全资子公司(即People公司)利益为手段的“联合存货采购计划”的实施,达到支持母公司(即 Wise公司)的目的。Wise兄弟的行为违反了其作为People公司之唯一董事,要求其考虑与保护People公司唯一的真正利害相关者——债权人 ——的义务。一审判决支持了债权人的诉讼请求,判决Wise兄弟偿付破产管理人44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但上诉审法院推翻了该判决,而最高法院则维持了上诉审法院的判决结果。
二各级法院判决理由
(一)一审法院判决理由概述
本案一审Greenberg法官认为,根据CBCA第122条(1)之规定,当公司破产或濒临破产时,董事的信义义务与注意义务应扩及于公司的债权人。Greenberg法官指出,当Wise兄弟为挽救两公司的财政厄运而实施“新政”(即“联合存货采购计划”)时, People公司已濒临破产境地,而“新政”的实施害及了People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作为People公司董事的Wise兄弟应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损害负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做出后,原、被告双方均提起上诉。
(二)上诉审法院判决理由概述
审理该案的魁北克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 Pelletier J. A. , Robert C. J. Q. , Nuss J. A. )一致同意支持Wise兄弟的主张。上诉法院判决表达了对遵从Greenberg法官所提出之判决理由的犹豫,并认为法律规则的创新(像 Greenberg法官判决中所创设的新规则,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与公司本身的最佳利益于公司破产或濒临破产时等同起来)是一个政策问题,国会比法院更适合于解决这样的问题。因此,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
(三)终审法院判决理由综述
终审法院(最高法院)在阐述其判决理由时首先指出,根据《魁北克民法典》(Civil Code of Québec,1991)第300条规定以及《法律解释法》( Interpretation Act, 1985)第8. 1条之规定,民法是诸如CBCA等联邦立法的补充法律渊源。既然CBCA未赋予公司债权人直接起诉公司董事的诉权,因此应转而从《魁北克民法典》中寻求法律支持,探寻在魁北克地区如何解释基于联邦制定法而创设的权利问题,特别是如何将CBCA第122条(1)之规定与民事责任法的基本原则协调起来的问题,也即成为恰当的问题解决之道。
CBCA第122条(1)确立了公司董事管理公司与监督公司管理时的两项互有区别的义务,即信义义务与注意义务。CBCA第122条(1)的规定是这样的:“公司的每一董事和管理人员在行使其职权和践行其职责时应当: ( a)以公司之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诚信行事; ( b)像一个理性人身处类似环境时践行其谨慎、勤勉与技能。”该条( a)项规定了董事的信义义务, ( b)项规定了董事的注意义务。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一审法官对该条规定所确立的两项董事义务未予以区别考虑并分别适用,“正如上诉审法院所指出的,一审法官似乎将这两项义务混淆在了一起。而实际上它们是有区别的,并分别承载着不同的立法目的”。有鉴于此,最高法院对这两项义务分别作了阐述。
1. 公司董事之法定信义义务
最高法院首先援引了新近的一个判例,即K. L. B. v. British Columbia案,[1]对普通法上的“信义义务”概念进行了界定。依K. L. B. v. British Columbia一案的主审法官Mclachlin的观点,信义义务可产生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而这些产生于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信义义务有一条共同的主线贯穿始终,即如忠诚、避免义务与利益的冲突、不得从受益人的损害中获利等,而“信义义务则将依产生它的法律关系的特殊本质的不同而改变”。在本案中,需要考虑的是基于董事与公司之关系而产生的信义义务的特殊本质问题。
在普通法上,董事的信义义务产生一种严格责任已是一条既定的法律规则,亦即董事不仅在以公司利益损害为基础而获取个人私利的情况下要负有责任,即使其个人获利并非以公司利益的损害为基础时,也可能负有归还其获利的责任。法律如此规定的理由在于,董事不得利用其职务身份获取利益。但该规则并不意味着,公司董事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从其诚信管理与监督公司经营的行为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个人利益。例如,在许多情况下,公司董事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公司董事同时也是公司股东,他们的红利将因公司财政状况的提高而提高,其作为公司董事的薪酬也将因此而增加,而董事的上述利益所得,并不因为是由公司支付的就当然地置其于违反信义义务的境地。因此,应综合考察个案中的所有情况来判定公司董事是否诚信地以公司之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行事。撰写终审判决的Pelletier法官指出:“就信义义务而言,我想要指出的是,Wise兄弟仅是出于要解决共同影响两家公司的存货采购问题的良好愿望而采取行动的,而这一动机(motivation)与CBCA第122条(1) ( a)所规定的追求公司利益的含义相一致,因此对Wise兄弟的行为不存在任何正当的批评。”如上所述,毫无疑问,两家公司都在为存货管理问题而苦苦挣扎, Wise兄弟经慎重考虑采取了新的管理策略,以期解决这一问题。在缺乏证据证明这一新的管理策略的实施是出于个人利益或不正当目的的情况下,同时在有证据证明新管理策略的采取是为了让两家公司都成为一个“更好的公司”的情况下,终审法院认为Wise兄弟作为People公司的董事并未违反其负有的信义义务。
本件上诉案并不涉及公司董事对公司股东所承担的非法定义务,而仅涉及由CBCA所规定的法定义务。就法定信义义务而言,很明显,“公司之最佳利益”一语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等同于“股东的最佳利益”。从经济角度而言,“公司之最佳利益”意味着公司财产的最大化。但长期以来法院就认为,公司董事在以公司之最佳利益为出发点妥善管理公司事务时,还应考虑各种各样的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任何一种在过去不可动摇的经典理论都必须屈服于现代生活的事实,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在今天,如果一个公司的董事欲考虑公司雇员的利益,没有人会认为其这样做并非诚信地以公司之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行事。同样地,如果公司董事欲考虑公司政策所意图追求的社会效应,但作为结果行为却偏离了公司政策,也不能说公司董事未诚信地考虑公司股东的利益。当然,如果公司董事为授予公司雇员以利益而完全无视公司股东的利益,则其违反了法定的信义义务。但是,如果董事们仅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对公司股东以外的其他人的利益予以得体的尊重,则不能说董事们违反了其对公司应承担的信义义务。终审法院认为,为判定公司董事是否以公司之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行事,在某种既定情况下考虑到所有的事实情况,公司董事将股东的、雇员的、供货商的、债权人的、消费者的、政府的以及环境的利益纳入考虑是恰当的。然而,公司命运的沉浮所自然引发的各种各样的利益转换并不影响CBCA第122条(1) ( a)规定的董事信义义务的内容。在任何时间里,公司董事都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并且不能将公司的利益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或其他利害相关者的利益混为一谈。如果公司处于盈利状态并且资金状况良好、经营前景看好,则公司股东的利益、债权人的利益以及公司本身的利益是彼此一致的。但这种利益的一致性会因公司财政状况的恶化而改变,公司股东的最终受益权将会因公司被宣告破产而变得毫无意义,公司董事也会为债权人利益而将管理权交给破产管理人。当公司濒临破产时,公司股东的剩余利益索取权也几近枯竭,因此股东将偏向于支持公司董事采取一些高风险的经营行为,以期带来潜在的高额回报从而最大化股东们的剩余利益。而面对同样境况,债权人则将偏向于支持董事们采取稳健安全的措施以最大化其债权偿还价值。
公司董事的信义义务并不因公司濒临破产而有所改变。“濒临破产”一语所表达的含义无非是指公司的财政稳定状况面临恶化。在评价董事行为时,如果其解决公司财政问题的诚信努力取得了成功,则股东的剩余利益得以维持,债权人的地位也得以提高;相反,如果不成功,也不能就此认定董事行为违反了其法定的信义义务。当公司面临财政危机时,公司董事有义务以公司之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诚信行事,通过谨慎的努力使公司成为一个“更好的公司”。当公司面临困境时,董事们只能以公司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行事,而不能为支持公司的任何其他利害相关者群体而行事。因此,公司之利害相关者们不能援引公司董事的法定信义义务对公司董事提起诉讼,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请求法律救济。加拿大法律有关公司利害相关者的规定是独特的。债权人仅是公司利害相关者群体中的一种,但其利益的保护却有多种途径。例如,债权人在公司财政状况恶化时,可根据CBCA第239条和第240条之规定,以公司名义提起派生性诉讼,或依第241 条规定提起压迫救济诉讼。终审法院认为,“广泛的压迫救济使得将CBCA第122条(1) ( a) 规定的董事的信义义务扩及于公司债权人的保护成为不必要”。
综上所述,公司的利害相关者可利用压迫救济诉讼或以违反注意义务为诉因(下文将述及)而请求公司董事承担责任,因此无需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放在 CBCA第122条(1) ( a)所规定的信义义务当中进行解读。并且,就本案的案情来讲,Wise兄弟并未违反其向公司承担的法定信义义务。
2. 公司董事之法定注意义务
如上所述, CBCA并未赋予公司债权人基于法定信义义务之违反而直接对抗公司董事的诉权,但这并不等于说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董事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诉权救济,在这一方面,《魁北克民法典》作为一种补充的法律渊源可资利用。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有两种,即合同责任和非合同责任。前者产生于公司董事对公司的合同债务承担个人担保责任之时,而后者产生于公司董事之个人可归责的行为。很明显,在本案中,Wise兄弟不能被判承担合同责任,因为其并未就公司合同债务提供个人担保,因此非合同责任的承担是仅剩的可能性。
在本件上诉案中,要判定公司董事是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非合同责任,有必要参照《魁北克民法典》第1457条之规定。该条规定:“每一个人都有义务遵守由具体的行为环境、习惯或法律课处的行为规则,以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当某人违反了上述义务时,他应对因其过错行为而给他人造成的任何损害负责并就该种损害负有补偿责任,不论该种损害在本质上是身体的、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也应对因他人的过错行为给其他人所造成的损害或由其掌管下的物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负责。”依该条规定,与公司董事违反注意义务从而应承担非合同责任密切相关的三个要素是:谁负有注意义务——“每一个人”,对谁负有义务——“其他人”,何种违反将导致责任——行为规则。很明显,公司董事涵摄于“每一个人”,“其他人”也包括了公司债权人。有判例对该条规定之广泛适用性的重要意义作了以下说明:“对1053条(即现在的1457条)的适用范围予以限缩是非常危险的,将导致非常多的值得救济的诉讼被拒绝,使得对许多的违法行为丧失相应的救济。”对《魁北克民法典》第1457条的语义解释在整体上与CBCA有关规定的语义是一致的。CBCA第122条 (1) ( a)规定了公司董事的信义义务,要求公司董事以公司之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行事;而与此不同的是, CBCA第122条(1) ( b)规定的公司董事注意义务并未特别指明该种义务受益者的主体身份。CBCA第122条(1) ( b)仅是规定“公司的每一董事和管理人员在行使其职权和践行其职责时应当****像一个理性人身处类似环境时践行其谨慎、勤勉与技能”。因此,公司董事之注意义务的受益者主体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概念,公司之债权人当然包括在内。对CBCA第122条(1) ( b)作这样的理解很显然与对民法典中之“其他人”的解释相一致。因此,如果公司董事违反了一定的注意标准,并且因果关系要件与损害要件全部齐备,债权人则可援引《魁北克民法典》第1457条之规定维护其债权。
接下来就是判定能够引发公司董事非合同责任的“行为规则”问题了。《魁北克民法典》第1457条第1段的规定并未具体表明行为标准,但对此可转引CBCA第122条(1) ( b)的规定加以补足。因为民法典第1457条第1段规定的注意义务是:“每一个人都有义务遵守由****法律课处的行为规则,以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而此规定中的“法律”当然包括CBCA在内。因此,在本案中要判定Wise兄弟是否应负有非合同责任,与之相关的仅是CBCA之规定,为此有必要对CBCA第 122条(1) ( b)规定中的注意义务要件加以探明。
董事之注意义务既是制定法规定的一项义务,也是普通法上长久以来即已确立的一项法律规则。在早期的一些英国判例中,即已确立了董事的注意义务。就实质上言,这些判例所确立的注意标准是一种主观标准。普通法要求公司董事在处理公司事务上避免存在重大过失,对公司事务的决断要依其个人的技能、知识、能力与才干。“就这一领域的判例法历史以及商业上通常占据优势地位的能力标准而言,在普通法上很显然公司董事并不被期望具有任何特别的商业技能或判断力。” 对CBCA之立法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加拿大新商业公司法立法建议》( Proposals for a New Business Corporations Law for Canada)[5]改变了传统普通法上的主观性注意标准,改采客观标准,要求公司董事的管理行为达到“理性人”的标准。该立法建议第9. 19条是这样规定的:“(1)公司之每一董事和管理人员在行使其职权和践行其职务时,应当: **** ( b)以一个理性人之小心、谨慎和技能行事。”CBCA第122条之(1) ( b)与上述立法建议第9. 19条之( b)基本相类似,但前者并非是后者的简单复制。二者的主要不同体现在,前者比后者在立法语言上增加了“在相似的情况下”一语,而这一不同改变了在做出某一判决时应纳入考虑的制定法标准所要求的因素,且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在注意标准中引入了主观性因素。因此,审理Soper v. Canada[6]一案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Robertson将CBCA第122条之(1) ( b)规定的注意标准称为“客观性的主观标准”,会导致对此标准在理解上的混淆。将CBCA第122条之(1) ( b)规定的注意标准概括为“客观标准”澄清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该条规定的注意义务中,围绕董事行为时的事实方面情况是重要的。这与规定于CBCA第 122条之(1) ( a)中的信义义务要求正好相反,在后者,董事行为时的主观动机是信义义务的核心点。
更加严格的注意标准要求给公司提高其董事会决议的质量施加了压力,而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规则将为保护公司董事免于遭受违反注意义务的起诉提供了一道屏障。但即使有了良好的公司治理规则,公司董事的决议仍然可能遭受来自公司外部利害相关者的批评。加拿大法院,就像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同行们一样,在判定与注意义务相关的案件时,倾向于尊重这样的事实,即公司董事通常是具备商业技能的,而法院则不具备。在商场上的许多决策,虽然最终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但在其做出之时却是合理的。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做出决策所依赖的详细信息并不充分,但由于时间的压力,董事们也不得不做出具有较高风险的决定。有些人喜欢以事后获得的信息来判断某一不成功的商业决策是不合理的或不谨慎的,但这仅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偏见。为克服这一偏见,加拿大法院发展出了一种抗辩规则,即“商业判断规则”。在Map le Leaf Foods Inc. v. Schneider Corp.案中, Weiler法官对商业判断规则做出了这样的阐述:法院关注的是董事的决策是否是合理的,而非是否是完美的。如果董事采取的决策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法院即不应以自己的观点取代董事会的观点,即使该决策的事后结果遭到了质疑也是如此。只要董事在几个合理的替代方案中选择了一个,就应给予董事会的决策以尊重。这一对董事会决策应予尊重的规则即是“商业判断规则”。董事拒绝采用替代交易的事实与此无关,除非能够证明某一特别的替代交易比已选择了的交易更具有可行性,并且明显的对公司更加有利。
原告要想成功挑战某一商业决策,就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方面要件:一是公司董事行为违反了其承担的注意义务,二是该种违反行为造成了原告的损害。如果董事谨慎行事并基于合理的信息基础行事,则董事们不会被判承担违反CBCA第122条之( 1) ( b)规定的注意义务的责任。依据董事们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所有事实情况,其所做出的决策必须是合理的商业决策。为判定董事们是否以违反注意义务的方式行事,有必要反复强调的是,法律并不要求公司董事的行为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法院在对公司做出决策时所考虑之商业技能的运用进行第二手的猜测时应持犹豫态度。但法院有能力在任何案件中,依据案件的事实情况决定,在行为当时,公司董事是否为获致一个合理的商业决策而付出了适当程度的谨慎与勤勉。
在本案中,原告的破产管理人声称Wise兄弟所实施的“新政”侵害了People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违反了CBCA第122条之(1) ( b)规定的注意义务。综合考虑本案所有的证据情况,终审法院同意了上诉法院的意见,认为“新政”实施的目的是为了矫正公司所存在的严重而又急迫的商业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在当时情况下又没有任何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可资采用,因而新政措施的采取是一个合理的商业决策。一审法官认为新政的实施无情地导致了 People公司经营的失败与破产,这一结论与事实不符,也是不正确的,因此一审判决犯了明显的应予推翻的错误。实际上,正如Pelletier法官所指出的,有许多其他因素而非“新政”更直接地导致了People公司的破产。一审法官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Wise兄弟并未从所谓的“疑问交易”中获取直接的好处,并且Wise兄弟在采取行动时是诚信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两家公司都面临的严重存货管理问题寻求解决之道。由于评估错误,一审法官也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People公司由于其提供给Wise公司的货物也收到了相当的回报。另外,就一审法官认定Wise兄弟应当承担责任的“新政”措施,终审法院的观点也与其正好相反,该措施的采取并非那么严重,也并非是导致People公司破产的真正原因。因此,终审法院的观点与上诉审法官的观点相同,即“新政”措施的采取并不说明Wise兄弟违反了CBCA第122条之(1) ( b)规定的注意义务。
另外,上诉审法院还引用了CBCA第44条(2)与第123条(4)之规定作为Wise兄弟免于承担注意义务的依据。CBCA第44条规定允许全资子公司给予其母公司以财政支持,该条之(2)是这样规定的:“一个公司可以采用贷款、担保或其他方式给予财政支持,向**** ( c)一个持股公司,如果该公司是该持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但终审法院认为, CBCA第44条(2)之规定并不能取代CBCA第122条(1)之规定,也不能免除公司董事依CBCA第122条(1)之规定而承担的注意义务违反责任。另外,Wise兄弟抗辩指出,其善意地信赖了公司财政副总裁David Clément作为一个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因此依CBCA第123条(4) ( b)[9]之规定应当免责。上诉审法院接受了Wise兄弟的该种抗辩理由,但终审法院对此不予同意。CBCA第123 (4)条是这样规定的:“****一个公司董事不能被判依第118条、119条或122条规定承担责任,如果其善意地信赖: ( a)公司管理人员向其提交的财务报表或公司审计人员提交的书面报告,而该报表或报告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政状况; ( b)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资产评估师或其他人提交的报告,而这些人的职业使其所提交的报告具有可信赖性。”尽管Clément获得过商学位,并在 Wise公司具有15年之久的从事财务管理的经验,但Clément的该种资历还尚不能达到允许Wise兄弟可以据此免除注意义务违反责任之抗辩事由的专家化水平。CBCA第123条(4) ( b)规定的职业群体是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资产评估师,而Clément并非会计师,其不受该职业组织规则的约束,也没有独立的职业责任保险。“财务副总裁”的头衔并不能自动地得出结论认为Clément的“职业使其所提交的报告具有可信赖性”。Clément仅是受雇于Wise公司的一个非专家性雇员,不能将其对解决公司存货采购管理问题方案的正当性判断作为专家建议。尽管这样的说法或许是可以接受的,即Clément比Wise兄弟在解决公司的存货采购管理问题的方案设计上具有更好的专业技能和职业地位,但这样的说法并不充分。因此依终审法院观点,Wise兄弟并不能依CBCA第123条(4) ( b)之规定成功地进行免责抗辩,其要赢得最终诉讼的胜利,必须另寻他径。
三案件述评
在英美公司法上,公司董事的义务可分为两种类型,即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后者有时也被称为公平交易义务,但对其更常用的称呼是“信托义务”,即“信义义务”。[11]公司债权人是否为公司董事信义义务之授信主体? 公司债权人是否为公司董事注意义务之权利主体? 上开加拿大最高法院在Peo2p les Department Stores Inc. ( Trustee of ) v. Wise一案中,对这两个问题分别进行了判决说理并给出了明确的结论,这在判例法的发展史上定会留下重重的一笔。接下来我们结合英美法的判例、学说及上开判例,就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之信义义务规则与注意义务规则分别做一简单的评析。
(一) 公司董事之信义义务
1943,美国联邦巡回法院Frankfurter法官在审理SEC v. Chenery Corp. 一案时指出:“说某人是受信人仅仅是分析的开始,这为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指明了方向。其是谁的受信人? 作为受信人其负有何种义务? 在哪些方面其未能履行义务? 其违反义务的后果是什么?”12]Frankfurter法官的一连串提问为我们探讨公司董事之信义义务问题搭建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与本文分析相关的是第一个问题,即公司董事是谁的受信人? 易言之,公司债权人是否是公司董事的授信人?
在上开判决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公司是公司董事之唯一授信人,申言之,不论公司是否濒临破产,公司债权人都不是公司董事之授信人,因此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不负有信义义务。加拿大最高法院所创立的这一判例规则符合普通法之传统规则。在普通法上,首开公司董事只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的著名判例是英国Percival v. Wright一案。该判决虽然只是一个初审法院的判决,但其所创设的规则却得到了普通法国家许多后续判决的支持。应当说,公司董事之义务仅针对其所供职的公司而并不扩及于公司债权人是普通法的一项基本法律规则,该规则为所有的普通法国家所接受,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以色列。同时,大陆法系国家往往也接受这一规则,如奥地利、意大利等国。[14]
美国律师协会商法分会公司法委员会( the Committee on Corporate Laws of the Section of Business Law of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认为:“公司董事可以考虑其他利害相关者的利益,但仅能到此程度,即公司董事们正在以公司股东和公司之最佳短期或长远利益行事。”《纽约州商业公司法》第717条( b)规定:“本节中没有任何一部分课处公司董事对任何人或组织以义务,要求其对前述人员加以考虑或提供特别的重视;本节中也没有任何一部分废除公司董事之义务,这些义务不论是由制定法规定的,还是由普通法认可的,抑或是由法院判决所确立的。”结合以上两项规定可以看出,在美国法上,公司董事对公司之利害相关者利益加以考虑是其权利而非义务,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不承担信义义务。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309条(1)规定:“公司董事在履行其职责时应考虑的因素包括公司雇员之整体的利益以及公司成员的利益。”[16]同时该条之(2)规定:“本条规定对公司董事所课处的义务,由公司董事向公司承担(并且仅向公司承担) ,并且该种义务的强制履行方式与公司董事对公司承担的其他信义义务的强制履行方式相同。”[17]由上述两项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法律并未将公司债权人之利益列入公司董事可以考虑的利益主体范围内;二是法律虽对公司雇员的利益做出了明确规定,但这并不等于说公司雇员可以直接针对公司董事提起诉讼,而该种诉权仍然属于公司。
综上,在英美法上,不论法律是否明确将公司债权人规定为公司之利害相关者,公司董事都不对公司债权人承担信义义务,因此公司债权人也无权针对公司董事以信义义务违反为诉因直接提起诉讼。加拿大最高法院之上开判决与传统普通法规则并无违背。美国明尼苏达州上诉法院对普通法采行此规则的理由作了这样的表述:“公司董事以及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在公司破产时,并不负有针对公司债权人的最小化因公司破产可能造成的损失的义务。如果公司的董事负有该项义务,则会使得公司(不论是有偿付能力的公司还是破产的公司)债权人不当地干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债权人的债务应当被偿付,这是不言自明之理。但在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公司债权人也不享有对公司董事及其他管理人员就如何采取经营管理行为发号施令的权利,这同样是不言自明之理。”
就我国现行公司法制而言,我国《公司法》第59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第118条第2款规定:“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由以上两项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公司法也仅认可公司是公司董事之授信主体,公司董事仅对公司承担信义义务,公司债权人不是公司董事之授信主体,也无权针对公司董事以信义义务违反为由提起诉讼。
(二)公司董事之注意义务
公司是依制定法而成立的一种法人组织,具有独立于其出资者(股东)的法律人格。它可以像自然人一样从事商业经营行为,也可以像自然人一样承担法律责任,而所有这些营业利益或法律责任都被视为公司自身的,因此现代公司成为了一种遮蔽和保护隐藏于其后自然人的一种法律机制。但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即公司只能通过隐藏于其后的自然人的行为从事经营活动,这些自然人就是公司的雇员,包括公司的高级雇员——公司董事。因此,公司董事具有双重身份,即自然人与公司机关。作为公司机关,公司董事之行为责任由公司承担。但作为自然人,其行为责任则由公司董事自己承担。
课处公司董事以法律责任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阻却公司董事滥用职权,二是补偿公司因其董事滥用职权所导致的损害。在公司法上,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两大原则置公司债权人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课处公司董事之滥权行为以侵权赔偿责任,可以使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恢复到董事职责未被违反时的状态。阻却公司董事之滥权行为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依靠市场自身力量,迫使公司董事依法行使职权,忠实履行职责。首先,如果公司董事的违法行为导致公司损害,公司股东将解除该董事的职务,从而迫使公司董事因惮于职位丢失而依法履行职责。其次,公司董事的业绩考察由公司的赢利水平决定,而公司董事的违法经营行为将导致公司利益的损害,也会使实施该违法行为的董事的名望受损。其结果必然是,如果该董事被解职,则其在未来之劳动力市场上想谋得一个满意职位和可欲薪酬的愿望即难以实现,从而迫使公司董事因出于珍惜自己的职业声誉考虑而依法履行职责。再次,按照现代公司的经营管理模式,公司董事的薪酬往往与公司的赢利水平相挂钩,这种分配模式将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市场驱动效应,从而激励公司董事谨慎行事,通过努力提高公司赢利水平来达到提高自身待遇的目的。但是上述单纯依靠市场自身力量来解决公司董事滥权问题的途径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种途径仅是一种理想化市场的选择,但因现实市场的无效率性和市场信息的不透明性,这种理想化的途径并不能达到(或在相当程度上无法实现)阻却董事滥权的目标。二是这种途径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阻却公司董事滥权的目标,但并不能实现补偿受害者损失的目标。众所周知,市场自身力量的阻却性因素并不能完全消除公司董事的滥权行为,这就为通过法律途径课处公司董事以法律责任、填补受害者损失的责任机制留下了存在的空间。于是就有了第二种途径选择,即通过课处公司董事以法律责任的方式,阻却公司董事实施违法经营行为。
在两大法系,就公司董事对其滥权行为给第三人造成损害时应承担责任的根据是不同的。在日本,有关公司董事对第三人之责任规定于其《公司法》的第 266条之(3) :“公司董事在履行其职责时具有恶意或重大过失,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该规定,日本学者就公司董事对第三人之责任性质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即特别法定责任说、特殊侵权行为责任说以及一般侵权行为特则说。根据特别法定责任说,董事对第三人所负法律责任不同于民法所规定的侵权责任,而是由特别法即公司法所规定的责任。董事若对其业务执行有恶意或重大过失,即使没有一般侵权行为要求的对第三人的加害故意或过失,亦应承担责任。根据特殊侵权行为责任说,董事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范围的确定,不适用《日本民法典》第709条关于一般侵权行为责任的规定,只有董事在加害第三人时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时,方可成立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特则说,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就是《日本民法典》第709条规定的一般侵权行为责任,只不过就轻过失可免责而已。目前,特别法定责任说为日本之通说,并为日本判例所采用。
在英美法,公司董事对第三人之责任(非合同责任即侵权责任)为一般普通法上的侵权责任,即注意义务之违反。“该种责任与公司董事对公司承担的责任相区别,其责任的根据是每个人对其他人所应承担的一般性注意义务。”英美法上公司董事承担个人责任之法理基础首先在于法律上“公平原则”的要求,即每个人都得承担由其个人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其次,课处公司董事对第三人以侵权责任还与有效阻却和经济效率的法律目标相合。如果担当公司机关者确信其行为之责任排他性地由公司承担,则法律阻却公司董事实施侵权行为的政策目标就必将大打折扣。再次,判令公司董事承担个人责任还与危险利益原则相一致,即公司董事从其危险行为中获取了一定利益,则不得逃避其危险行为所造成的不利后果。
公司董事违反注意义务应对公司债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公司董事之作为或不作为导致公司债权人财产损害;二是公司董事之作为或不作为导致公司债权人人身损害;三是公司董事之过失陈述导致公司债权人经济上损失;四是公司文件特别是公司章程之误导性陈述导致债权人损失。
我国现阶段也有法律就公司董事对第三人之责任问题有所涉及。如《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条规定意味着发行人、证券公司的董事在该情形下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我国立法规定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首次突破。与《证券法》相比,我国《海南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 (1992年8月15日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在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范围上规定得更宽。该《条例》第106条对董事向第三人承担责任做出了这样的规定:“董事履行职务犯有重大过错,致使第三人受到损害,应当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开创了我国公司法在这方面立法的先例。但现行《公司法》对此问题却未予涉及,即我国尚没有要求公司董事对公司第三人(包括债权人)承担责任的一般性立法。依我们之见,我国既然采民商合一制,公司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对公司法未作明确规定的事项,当然可将民法的一般性规定作为其补充渊源加以适用。因此,上开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决以及英美法的通行做法可资借鉴。
「注释」
[1][2003]2S.C.R403,2003SCC51.
[2]根据CBCA第241条(2) ( c)之规定,如果公司董事行使职权的方式造成了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压迫,或不公正的歧视,或不公正的否定,则法院有权给予救济。
[3]See Regent Taxi Transport Co. v. Congrégation des Petits Frères deMarie,[ 1929 ] S. C. R. 650, perAnglin C. J. , at p. 655.
[4]See Dovey v. Cory,[ 1901 ] A. C. 477 (H. L. ) ; re Brazilian Rubber Plantations and Estates, Ltd. ,[ 1911 ] 1 Ch. 425 (C. A. ) ;and re City Equitable Fire Insurance Co. ,[ 1925 ] 1 Ch. 407 (C. A. ) .
[5]该立法建议发表于1971年,是由加拿大联邦政府任命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为制定新的联邦商业公司法而提出的,该立法建议发表于CBCA正式制定的四年前,对CBCA有重大影响。
[6][ 1998 ] 1 F. C. 124, at para. 41.
[7](1998) , 42 O. R. (3d) 177.
[8]该条规定在本案的疑问交易实施时还有效,但此后即被删除。
[9]该规定现已变更为CBCA之第123 (5) .
[10]See Robert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in a nutshell, 4 th ed, West Publishing Co. , 1996, p. 378.
[11]我国香港学者何美欢教授把“fiduciary”一词译为“信义”,而把“fiduciary duty”一词译为“信义义务”。参见何美欢著:《香港代理法》(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与第十五章。
[12]318 US 80 (1943)。
[13](1902) 2 Ch 421.
[14]See Zipora Cohen, Directors‘Negligence Liability to Creditors: a Comparative and CriticalView, 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2001(winter) , p. 354.
[15]See Committee on Corporate Law,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Other Constituencies Statutes, Potential for Confusion, 45 BUS LAW2269 (1990) .
[16]CompaniesAct of 1985, c. 6, §309 (1) .
[17]CompaniesAct of 1985, c. 6, §309 (2) .
[18]St James Cap ital v. Pallet Recycling Ass‘ns of N Am, Inc, 589 N. W. 2d 511, 516 (Minn. Ct App. 1999) .
[19]参见刘俊海:《股东权法律保护概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20]See Saucier v. U. S. Fid. Guar Co. , 280 So. 2d 584, 585 - 86. (La Ct. App 1973)
烟台大学·房绍坤 王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