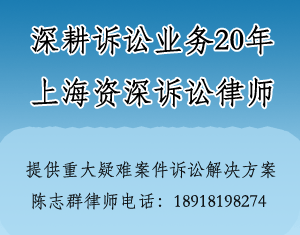根本违约制度起源于英国判例法,19世纪英国法院开始把合同的条款划分为“条件”和“担保”两类,“条件”是合同中重要的、根本性的条款,“担保”则是合同中次要的和附属性的条款,当事人违反不同的条款,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一方当事人违反“条件”,另一方当事人不仅可以要求赔偿,而且有权解除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担保”,另一方只能请求赔偿而不能解除合同。法官在论述违反“条件”时,使用了“本质上违反合同”、“根本上没有履行合同”、“动摇了合同根基”等提法,这是英国判例法中“根本违约”一词的源出。到本世纪50年代,英国法官试图运用根本违约来排除各种不公平的免责条款的使用,他们主张如果一方违反合同义务以致动摇了合同的根本时,则不得利用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逃避违约或侵权责任。而违反“条件”理论使当事人和法院可以比较容易地对违约能否导致合同解除作出判断,但是,根据这一理论,即使对方处在并未因此遭受损害或损害极其轻微的情况下,违反“条件”一方当事人也可能承受来自对方解除合同的后果。到了二十世纪,格式合同的出现和普遍运用使契约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经常规定“不论实际情况如何,该组织概不负责”,这是明显违背公平原则的,于是,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法院对违反“条件”理论进行了重大变革,在契约自由与禁止滥用免责条款之间寻求某种公平的衡平制度[1]。英国法开始以违约后果为根据来区分不同的条款,认为“违反某些条款的后果取决于违约所产生的后果”,违约违反的是属于条件还是担保条款,主要取决于违约事件是否剥夺了无辜当事人“在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本来应该得到的实质性利益”。这实际上反映的是“条件”和“担保”以外的第三种条款,即所谓“中间条款”。“中间条款”理论的出现为法官根据违约造成的客观后果而不是根据被违反条款的性质来断定当事人一方是否有权因对方违约而解除合同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准和思维方法。此时,根本违约已不再是违反条件的同义语,而是指任何足以使受害方有权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
美国法与英国法不同,没有使用“根本违约”的概念,而是采用“重大违约(materialbreach)”或“根本性不履行(substantialnon-performance)”概念,把违约分为轻微违约和重大违约,一般只有构成重大违约,非违约方才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之可能(因为有时即使构成重大违约,非违约方也不能立即解除合同,而应先给予违约方充分的自行救济机会)。但实质上这一标准不适用于货物买卖合同,如果货物或提示交付的单据在任何方面不符合合同,即使轻微违约,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买方可以全部拒收货物(《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01条)。至于是否构成重大违约,《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次)》第241条规定的主要考虑因素是:(1)受损害方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他从合同中应得到的合理预期的利益;(2)受损害一方的损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适当补救的;(3)如果受损害一方终止履行,有过失一方在多大程度上会遭受侵害;(4)有过失一方弥补过失可信度;(5)有过失一方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善意”与“公平交易”准则[2]。那么,法官在判案中认定根本违约时如何适用呢?是只具备其中一个因素即可,还是同时具备五个因素才行呢?有没有一个份量比较重呢?纽约州上诉法院法官西巴黎克(Ciparick)在最近一个案例中指出,是否适用“严重违反合同”理论,首先要看有过失一方会不会遭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损害(即第3种因素)[3],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美国法院在判定重大违约时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违约的受损害方有权期待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大程度被剥夺了(即第5种因素)[4]。因之,美国的重大违约作为合同解除权的限制条件不具有绝对性,且其判定标准复杂,缺乏明确的适用顺序,具有不确定性,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给非违约方利用解除合同进行违约救济制造了障碍,使其无所适从。
大陆法系并无根本违约的概念和统一标准。《法国民法典》第1184条虽然规定债权人于债务人一方违约(不论严重是否)时可通过法院来解除合同,但是法国法院往往将债权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严重作为合同解除的一个重要判定标准[5]。《德国民法典》第326条及第326条规定了给付不能(包括全部给付不能与部分给付不能)、给付迟延(包括定期债务的给付迟延与非定期债务的给付迟延)情形的合同法定解除条件,但其实质是以违约后果的严重性(即根本违约)作为判定标准,不过根本违约判定标准系结合具体违约形态的分析来体现的。显然,《德国民法典》既未像法国法及英国判例法那样简单地界定根本违约的定义,也未像美国那样抽象地囊括根本违约判定标准的综合考虑因素,做到形散而神似,将根本违约判定标准之抽象概括(即违约造成的后果严重致使合同预期目的的不能实现)化解在具体违约场合之下,其立法模式更具科学性。
吸纳了两大法系立法成果《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称《公约》)使用了“根本违约”一语,并明确规定了根本违约的标准界定,即“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至于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第25条)。但是,《公约》第25条规定的可预见性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往往会限制非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使其不敢贸然采取解除合同之违约救济措施;同时,《公约》第49条、第51条、第64条、第72条、第73条规定的具体违约判定标准并无《公约》第25条所规定的可预见性标准之要求,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矛盾,这也使得非违约方解除合同予以救济时往往举棋不定。
在我国已失效的《中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9条规定: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以致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或合同一方当事人在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而且在被允许推迟履行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与《公约》相比较,我国涉外合同法抛弃了主观标准,没有使用预见性理论来限定根本违约的构成,减少了因主观标准的介入而造成的随意性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另外,在违约的严重性的判定上,涉外合同法采用了“严重影响”的概念来强调违约结果的严重程度,而没有使用“实际上”剥夺另一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这就使判断根本违约的标准更为宽松。实践证明这种规定是切实的、合理的[6]。在借鉴和吸收包括《涉外经济合同法》在内的三部合同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中国统一合同法,关于根本违约的规定又比《涉外经济合同法》更为合理。该法第94条第4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尽管在此规定中并没有使用根本违约的概念,但已充分体现根本违约制度的思想。“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强调了“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的严重后果是“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从违约后果的严重性出发来判断是否为根本违约。同时,该条还规定了: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以上解除合同的情形均可以归纳为违约所造成的结果严重,使合同目的落空或不可期待,实即根本违约。
但是,我国《合同法》虽在分则的买卖合同、承揽合同等有名合同中规定了瑕疵履行及部分违约的根本违约适用标准,但这些规定显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合同类型。民法作为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具有引导、规范人们日常行为模式之功能,《合同法》第94条第4款“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缺乏操作性且未考虑不同违约形态之个性差异,过分抽象、模糊的法律语言显然难以胜任这一功能。因此,应将拒绝履行、瑕疵履行及部分违约情形的根本违约判定标准补充到《合同法》的合同法定解除制度中,既便于人们日常民商事交往的合理行为预期安排,又能使法官裁判具有确定性的依据。
笔者认为根本违约判定标准应脱掉其抽象外衣,结合具体违约形态来分析合同法定解除权之合理行使,界定根本违约的具体判定标准。根据合同目的是预期还是实际不能实现、是部分还是全部不能实现之标准,结合具体违约形态对根本违约具体判定标准可作如下类型分析:
1. 预期根本违约判定标准。预期违约,包括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是英美法系特有的法律制度。大陆法系无预期违约概念,而有与默示预期违约规则相类似的不安抗辩规则,虽然二者在性质、适用范围、成立条件及权利救济措施等方面存有差异[7],但仍存在联系:一方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后,对方的行为状态往往是抗辩权人借以推知其是否构成默示预期违约的基本条件之一[8]。正因为如此,两规则可同时规定在同一合同法中。《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09条规定即是例证,该条第1项规定了不安抗辩内容,第4项实质上是默示预期违约制度规定。我国《合同法》采用了与《美国统一商法典》不同的立法技术,将不安抗辩规则置于“合同履行”一章,而将预期违约作为违约形态规定于合同解除和违约责任的相关章节。
明示预期违约情形,即合同有效成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一方当事人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表示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时,便构成根本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默示预期违约情形,预期违约方并未将到期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意思表示出来,另一方只是根据预期违约方的某些情况或行为(履行义务的能力有缺陷、商业信用不佳、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行为表明有不能或不会履行的危险等)来预见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此时可以终止自己相应的履行并要求对方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其能够履行的保证;若对方未能在此合理期限内提供履行保证,即构成根本违约,预见方才可以解除合同。
2. 实际根本违约判定标准。实际违约形态包括履行不能、拒绝履行、迟延履行及瑕疵履行,各种违约形态的违约程度不一,因此构成根本违约的具体判定标准也不同,有必要再作具体分析:(1)履行不能情形的根本违约判定标准。履行不能是指债务人在客观上已经没有履行能力,如以特定物为标的的合同,该特定物毁损灭失,以种类物为标的的合同中,种类物全部毁损灭失。履行不能即属合同目的无论是因债务人之原因,还是因债权人之原因或者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原因不能实现,构成根本违约,致合同履行不能债务人或债权人均可解除合同。(2)拒绝履行情形的根本违约判定。拒绝履行是指履行期限届满时,债务人能够履行债务而故意不履行。由于拒绝履行与预期违约在是否可以消除违约状态、撤回拒绝履行的意思表示及赔偿范围上存有差异,同时,虽然与迟延履行一样均违反了履行期限的要求,但是二者在违约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补救方式上显有区别,因此应将拒绝履行界定为履行期限届满后的故意不履行而与预期违约相区别。拒绝履行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违约,违约方故意不履行合同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属根本违约,非违约方此时有权解除合同。(3)迟延履行情形的根本违约判定标准。迟延履行指债务人能够履行,但在履行期间届满时却未履行债务的现象。构成迟延履行必须具备四要件:存在着有效的债务;能够履行;债务履行期间已届满;债务人未履行。迟延履行包括定期债务的迟延履行和非定期债务的迟延履行。定期债务迟延履行场合,根据合同性质或者当事人的约定,履行期限是合同履行的根本条件,若当事人一方不在特定时间履行,不能达到合同目的,则构成根本违约,相对方无须催告,即有权解除合同。非定期债务迟延履行场合,根据合同的性质,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内容上不特别重要,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时,相对人应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履行债务,如该期限届满仍未履行的,说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即构成根本违约,相对人有权解除合同。(4)瑕疵履行情形的根本违约判定。瑕疵履行指债务人虽有履行,但其履行(如质量、地点、方式等,履行数量有瑕疵属迟延履行)有瑕疵或者给债权人人身、其他财产造成损害,或给与对方债权人有特定关系的第三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包括不适当履行和加害给付两种类型。不适当履行场合的根本违约判定标准,德、法、日等国立法及《公约》、《通则》并无明确规定,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王泽鉴主张可类推适用迟延履行及履行不能之根本违约判定标准:不适当履行能够补正的,债权人得定相当期限催告其补正;如于此期限内仍不补正时,则构成根本违约,债权人可解除合同;惟非于一定时期履行则不能达合同目的者,即为根本违约,可不经定期催告而径直解除合同;履行上的瑕疵不能补正者(如特定标的物已不可能修理),即属根本违约,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加害给付一经发生,不仅使债权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且对债权人及第三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当然构成根本违约,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9]。
3.根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不同,根本违约又可分为全部根本违约与部分根本违约。前者是指致使合同目的全部不能实现的违约行为,后者则指导致合同目的部分不能实现的违约行为。履行不能、拒绝履行、瑕疵履行、迟延履行及预期履行均存在全部违约与部分违约之分。前述各种具体违约形态根本违约标准之确定,是就全部违约分析而言的。若为部分违约,而合同内容为可分者,致使该合同部分目的不能实现,则构成部分根本违约,债权人可就该部分合同予以解除;但合同内容不可分者,部分违约致使合同目的全部不能实现,则构成根本违约,债权人可就合同全部予以解除(《德国民法典》第325条第1款第3项、第326条第1款第3项、《意大利民法典》第1464条、《日本民法典》第543条、《公约》第73条)。
当然,根本违约制度的重要意义,主要不在于使债权人在另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获得解除合同的机会,而在于严格限定解除权的行使,限制一方当事人在对方违约以后滥用解除合同的权利[10]。这一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合同是当事人自由协商而达成的合意,是当事人筹划自己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社会生活而进行的行为预期安排。但是如果当事人一方存在违约行为,不论轻微或重大,另一方过分轻易解除合同,不仅对违约方构成重大损害,而且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根本违约的形式价值在于合理限制合同法定解除权,实质意义在于给予违约方更多的自行救济机会,避免因轻微违约而遭受不利益,促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为违约方利益与非违约方利益、非违约方利益与社会利益之冲突寻求一个理想的平衡点[11]。
--------------------------------------------------------------------------------
[1] 何宝玉,《英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81
[2] 徐罡,等 美国合同判例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P140—141)
[3] 徐罡,等 美国合同判例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P140—141)
[4] 王军 美国合同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P319—326)
[5] 尹田 法国现代合同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P349)
[6] 曹诗权.朱广新.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探讨[J].中国法学,1998,(4).
[7] 杨永清 预期违约规则研究〔A〕 梁慧星 民商****丛(第3卷)〔C〕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P357—358)
[8] 叶林 违约责任及其比较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P200—201)
[9] 张俊浩 民法学原理〔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P547)
[10] 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P543)
[11] 伍治良, 根本违约判定标准功能之回归研究, 法律科学,2002年第3期(总第118期)
(作者:彭春桃律师)